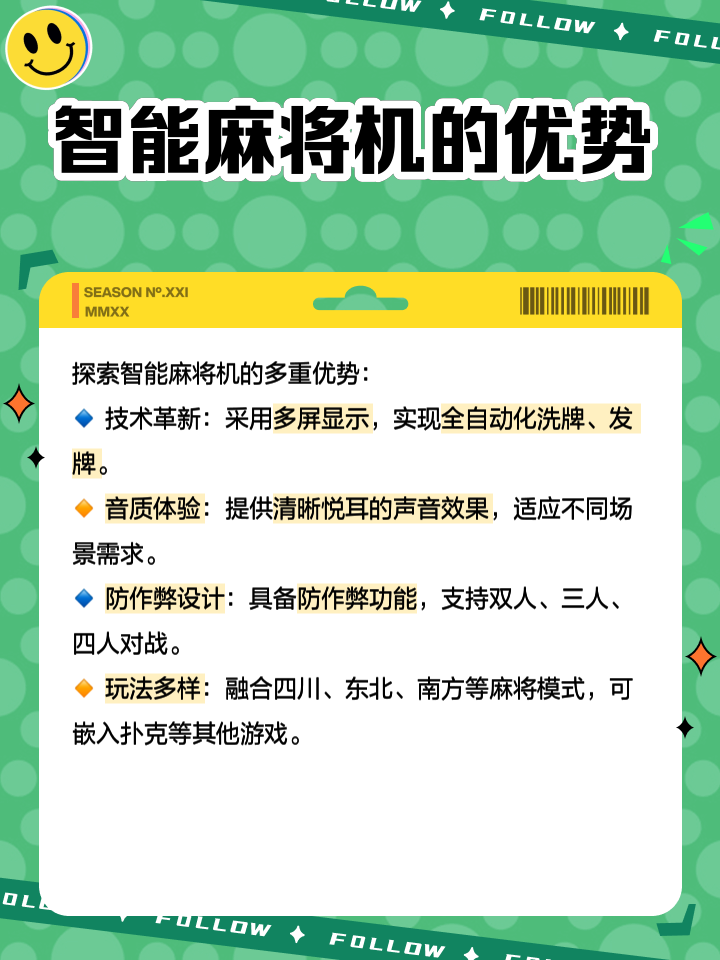麻将机少牌
那台麻将机是去年春节前买的,它来的时候,裹着厚厚的泡沫和硬纸板,像一尊被请进家门的现代神祇,父亲绕着它走了三圈,才小心翼翼地按下那个绿色的电源键,一阵轻快的运转声后,四排长城齐刷刷地升起,分毫不差,十四张牌静静地立在每个人面前,像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。
就是从那时起,家里的牌局变了味道。
过去手洗牌时,哗啦啦的声响能填满整个客厅,那是温热的、充满人气的噪音——牌与牌的碰撞,夹杂着姑妈的唠叨、姨父的笑话、父亲慢条理斯的点评,谁和了一张好牌,大家会传阅那张关键牌,摩挲着上面的刻痕;有人手气不顺,母亲会笑着说“我给你摸摸牌转转运”,那些竹背麻将经过无数双手的抚摸,边缘都已温润如玉。
而现在,一切交给那台沉默的机器,它精准、高效、无情,按下按钮,一百四十四张牌在它腹中轰隆隆地翻滚、排列、推送,我们只需坐着,像四个等待喂食的婴儿,谈话的间隙变得尴尬——再也没有洗牌的那三分钟让我们自然地喝水、调侃、聊聊家常,我们只是等着,等机器完成它的工作。
故障发生在一个周日的下午。
“停一下。”表哥突然说,“我的牌好像少了。”
我们数了一遍:十三张,再数一遍,还是十三张,每个人都开始数自己的牌——十三,十三,十三,十三。
“机器里还有牌没出来吧?”姑妈说着,拍了拍机器的顶部,像在拍打一头不听话的牲口。
父亲按下升降键,牌桌缓缓升起,我们看见了机器的内脏:错综复杂的轨道、转盘、磁铁,但那里空空如也,干净得令人不安。
少了一张牌。
不是东风白板,不是任何一张决定胜负的关键牌——少了一张最普通的三条,就是那张三条,竹背上的刻痕比其他牌略深一些,母亲总说它像一只飞走的小鸟。
我们在客厅里展开了地毯式搜索,沙发底下,茶几缝隙,花盆后面,甚至检查了每个人的口袋——什么都没有,那张三条就这样从世界上蒸发了,从一台完全封闭的机器里。
“不可能啊,”父亲反复说,“机器又不会吃牌。”
但牌确实不见了,在确认这一点的瞬间,某种东西在房间里悄然变化,我们面面相觑,第一次意识到:当一副牌不再完整,这局游戏就永远无法真正结束,那张缺失的牌成了房间里的大象,一个所有人都知道却不愿提及的秘密。
姑妈突然笑了:“少了张三条也好,你爸就胡不了清一色了。”
表哥接口:“说不定是牌自己跑出去旅游了。”
我们也都笑起来,继续用剩下的牌打着,规则临时修改:如果有人听三条,可以宣布“呼叫三条”,然后从牌堆末尾摸一张代替,游戏还在继续,但每个人都心照不宣——我们不再为输赢而战,而是在共同守护一个脆弱的谎言:这副牌依然是完整的。
说来奇怪,自从少了那张牌,牌局反而活了过来,我们开始创造新的规则,为那张永远缺席的三条编造故事,表嫂说它去环游世界了,小侄女说它变成了真正的鸟儿飞向窗外,我们甚至为它设了一个“专属座位”——一张倒扣的空椅子,仿佛那张牌正以隐形的方式参与我们的聚会。
那台麻将机依然立在客厅角落,它还是会准时在下午两点启动,还是会把剩下的牌码得整整齐齐,但我们不再完全依赖它——最后两局,我们一定会把手伸进牌池,亲手搅乱那些温润的竹块,让哗啦啦的声响重新充满房间。
少了那张牌之后,我们反而找回了什么。
也许完美的圆满本就是幻觉,就像一台永不出错的麻将机,一个永不散场的春节。真正维系我们的,从来不是毫无瑕疵的完整,而是共同面对缺憾时,那份心照不宣的温柔,与依然愿意坐下对弈的从容。
那台沉默的机器依然在角落里等待着,而我们已经学会,在缺一张牌的局里,把人生这场牌,打得风生水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