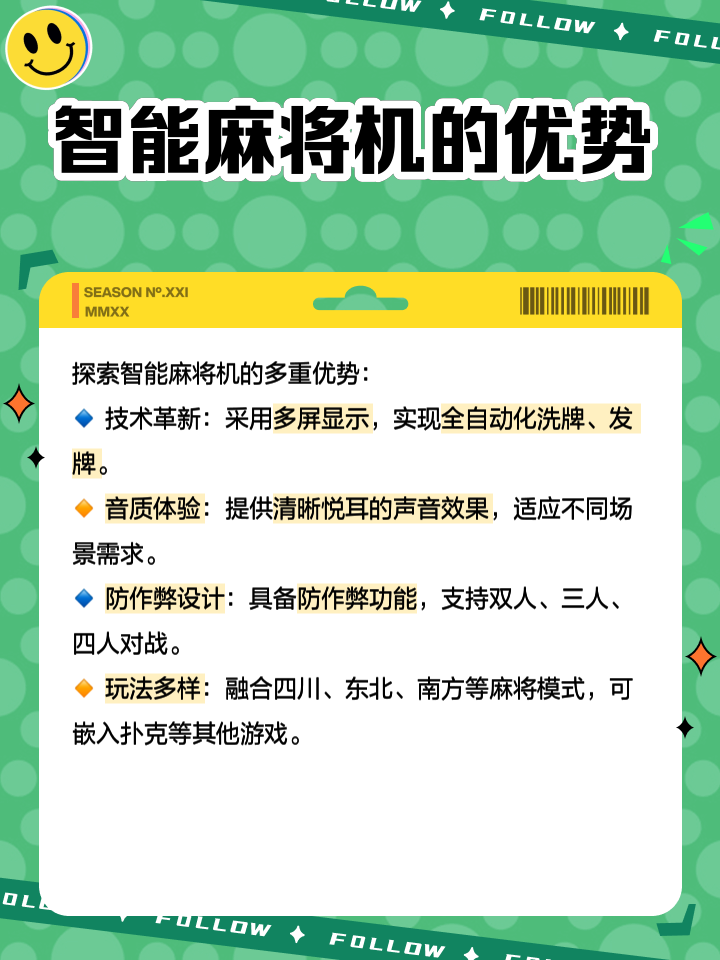程序麻将机农家乐娱乐
算法里的骰子声
我们选的是山坳里的一家,车子弯弯绕绕地开进去,路旁的竹林渐渐密了,才看见一角翘起的飞檐,院子是水泥铺的,打扫得倒还干净,最惹眼的,是廊檐下并排摆开的四张自动麻将机,机器是崭新的,深蓝色的台面,在午后懒洋洋的日光下,泛着一种工业制品的、过于完美的光,我们一行人刚下车,目光便不约而同地被它们牵了去。
朋友是老客,轻车熟路地开了电源,一阵极轻微的、属于电机的嗡鸣声响起,代替了记忆中那哗啦啦如山溪奔流的、骨牌与骨牌的热烈撞击,不多时,四家牌便已码好,齐整得像一列列待检阅的士兵,沉默地嵌在机器腹中,我们入座,手指按上那冰凉的、塑料质感的骰子键,清脆的“嘀”声之后,便是开局。
起初,大家还有些许置身乡野的新鲜感,会抬头看看远处青黛的山峦,评论几句菜畦里长势正好的青菜,几圈牌下来,心神便全被那小小的牌桌箍住了,这机器洗牌太快,几乎不容你有一刻走神,方才的牌局刚散,指尖的烟还没抽完,底下便已传来那熟悉的、沉闷的滚筒转动声,新一轮的“城墙”又已筑好,这效率是高得近乎冷酷了,它将等待的、闲谈的、属于旧式牌局的那些温吞的间隙,全都无情地剔除掉了,娱乐,在这里变成了一件高度浓缩、目标明确的事。
我的手气似乎出奇地好,好得有些不自然,想要“筒子”,摸上来的便是“筒子”;刚听“三六万”,下一巡自摸的便是“三万”,起初的兴奋渐渐褪去,心里反倒生出一种莫名的虚浮来,这胜利来得太轻易,太精准,仿佛不是自己搏来的,而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,稳稳地、预先安排好了递到你手中的,我偷眼去看朋友们,他们或蹙眉,或沉吟,脸上也并无往日常见的、那种全神贯注的紧张或豁然开朗的喜悦,倒像是一群被设定好程序的傀儡,在执行一场已知结局的演练。
中场休息,我踱到院角的水龙头旁洗手,山泉水凛冽,激在皮肤上,让人精神一振,这时,我看见隔壁那桌的几位老者,他们用的,是一副老旧的、边角已磨得温润的竹背麻将,那才是真正的“洗牌”,苍老的、布满褶皱的手,缓慢而有力地推动着面前的牌,发出一种厚重而踏实的“哗哗”声,那声音里,有岁月的包浆,有人手的温度,他们一边洗,一边不慌不忙地聊着今年的收成,孙儿的学业,那牌局,仿佛是嵌在生活里的,是生活的一部分,而不是生活的全部。
我忽然明白了我的不安源于何处,那程序麻将机,它提供的是一种被提纯、被保证的“乐”,它过滤了过程中的一切偶然与期待,它太完美,太公平,反而失却了那份人手码牌时,因力度、心境的不同而带来的,微妙的、属于“人”的偏差与趣味,我们追求的,本是在不确定的人生里,那一点点可以握在手中的、实实在在的运气;而机器给予我们的,却是一场被算法精心计算过的、空洞的确定性。
回到牌桌,我忽然觉得那光滑的蓝色台面,像一片深不见底的、被规训过的海,我们在此间的嬉笑与懊恼,或许,都只是漂浮在算法之上的一层薄薄浮油罢了,那遥远的、真实的骰子声,终究是再也听不见了。